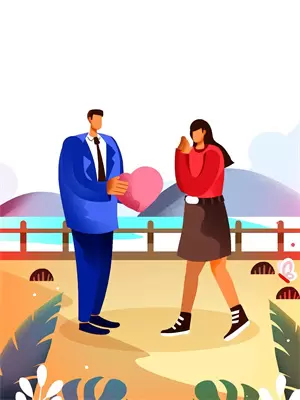- 五代离歌:琵琶血笺
- 分类: 军事历史
- 作者:澜星砚
- 更新:2025-08-12 19:44:14
阅读全本
《五代离歌:琵琶血笺》中的人物沈青芜李克用拥有超高的人收获不少粉作为一部军事历“澜星砚”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不做以下是《五代离歌:琵琶血笺》内容概括:当长安的火光舔舐着朱雀街的青石十六岁的乐伎沈青芜攥紧了怀中的琵那把刻着 “永保太平” 的老是她从灭唐的兵燹中抢出的唯一念却不知此后五十余它将成为记录乱世的刀
五代十国的烽烟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她见过白马驿的河水染红了文人的紫听过李存勖从 “三矢复仇” 的英雄沦为戏子皇帝的荒亲历过石敬瑭割让燕云契丹铁蹄下百姓的哀一把琵断了又弦上浸过血与琴身刻满流亡的地名 —— 汴梁的刀光、洛阳的伶声、太原的烽火、江南的残都在指尖震颤中凝固成历史的碎
与史官陈循的约让她从被动逃亡者变为主动记录在冯道的 “圆滑” 里看见生存的韧在柴荣的改革中触摸乱世的微却终究在陈桥驿的黄袍加身读懂历史循环的无她救下说契丹话的孤儿阿将《教坊记》的残页与血泪见闻一同藏进琴最终凝结成那部《琵琶血笺》。
这不是帝王将相的权谋史而是一个女子用琴弦丈量乱世的长当琵琶声在江南的月夜消那些浸在血里的字迹仍在低语:所谓乱从来不是岁月的断而是人性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坚守 —— 就像琴身刻痕里那朵永不褪色的血在灰烬中倔强地绽
沈青芜的布鞋在逃亡路上磨穿了底,露出的脚趾被河滩碎石划得血肉模糊,每走一步都像踩着碎玻璃,血珠混着泥水在沙地上拖出蜿蜒的红痕,没等干透就被后面的人踩成更深的污渍。
她怀里的琵琶被搂得死紧,桐木琴身被体温焐得发烫,琴箱里衬的软绸磨着锁骨,倒像是母亲临终前最后一次抚摸她的手。
那把琵琶是母亲的陪嫁,琴颈背面刻着极小的 “永保太平” 西个字,还是开元年间的老物件。
沈青芜总觉得那西个字里藏着母亲的魂,只要攥着琴,就不算彻底被抛在这乱世里。
“快走!
瞎磨蹭什么!”
粗粝的马鞭带着风声擦过耳畔,抽在旁边的芦苇丛里,惊起一群白鹭扑棱棱飞起。
沈青芜踉跄着往前扑,额头撞在前面妇人的背上,那妇人回过头,脸上满是煤灰般的污渍,唯有一双眼睛亮得吓人,像两簇濒死的炭火。
“小娘子,惜命就别停步。”
妇人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前儿个有个姑娘掉了队,被兵爷们拖进芦苇荡,出来时…… 只剩半截身子了。”
沈青芜猛地攥紧琵琶,指节泛白。
脖颈上还留着教坊司那串铜铃的勒痕,三天前朱温的士兵撞开宫门时,她就是被那串铃链拴在廊柱上。
铜铃在她挣扎时叮当作响,和姐妹们的哭嚎、士兵的狞笑混在一起,成了她对长安最后的记忆。
她眼睁睁看着教坊司的嬷嬷被一刀割破喉咙,鲜血溅在《霓裳羽衣曲》的曲谱上,把 “云想衣裳花想容” 染成了黑红色。
一阵更浓重的腥甜被风卷过来,带着河泥的腐臭。
沈青芜突然顿住脚步,像被看不见的线钉在了原地。
离岸半丈的浅水里,漂着个裹着紫袍的身影。
花白的胡须散开在浑浊的水面,像一蓬沉溺的水藻,而本该束着玉带的脖颈处,只剩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暗红的血在水里氤氲开来,像幅被揉皱的劣质水墨画。
沈青芜死死捂住嘴才没让尖叫冲破喉咙 —— 那身紫袍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章服,她在长安教坊司见过御史大夫穿同款,去年上元节,那位大人还捻着胡须听她弹《梅花三弄》,夸她 “指尖有风骨”。
“看什么看!
找死啊!”
押送的士兵踹在她后腰上,力道大得让她往前扑进水里。
冰凉的河水瞬间浸透粗布衣衫,冻得她牙关打颤,怀里的琵琶却被她高高举着,生怕沾了水。
挣扎着抬头时,视野里突然挤满了浮尸,像被秋风打落的残叶。
有的被箭钉在芦苇根上,箭杆上还挂着破烂的官袍;有的被拦腰斩断,肠肚在水里缓缓散开,引来成群的小鱼啄食;最让她脊背发寒的是个穿绯色官服的老者,怀里紧紧抱着一卷书,书页被水泡得发胀,露出 “论语” 两个洇湿的墨字,墨迹在水里晕开,像两行无声的泪。
“这是白马驿那帮老东西的下场!”
旁边的士兵啐了口唾沫,靴底碾过滩涂上的碎骨,“朱王说了,这些读死书的,总想着恢复大唐那套规矩,留着就是祸害!”
他突然扯住沈青芜的头发,把她的脸往水面按,“看清楚了!
以后见了咱们梁军的爷们,就该把头埋进裤裆里!
别学这些酸儒,死到临头还端着架子!”
河水呛进鼻腔,又辣又腥。
沈青芜在挣扎中看见那老者怀里的《论语》,突然想起母亲藏在《教坊记》夹层里的那句话:“乱世最狠的,从不是刀兵,是把人命当草芥的心思,是把诗书当粪土的狂妄。”
她猛地挣脱士兵的手,咳出满口河水,喉咙里火烧火燎地疼。
傍晚时分,她们被赶进一处临时搭建的营寨。
木栅栏歪歪扭扭,到处是没清理干净的血渍和粪便,几头瘦骨嶙峋的战马拴在桩上,啃着带泥的芦苇根。
沈青芜被两个士兵架着胳膊拖进最大的那顶帐篷,掀开帐帘的瞬间,浓重的酒气和血腥味扑面而来,熏得她几乎晕厥。
帐中央燃着个黄铜炭炉,火苗舔着炉壁,映得围坐的几个将领脸色忽明忽暗。
为首的络腮胡将军正举着个白玉酒杯,里面盛着暗红色的液体,在火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他对面的瘦高个将领谄媚地笑着,手里把玩着颗骷髅头,天灵盖上钻了个孔,用银链穿着,杯里的酒正顺着孔往骷髅头里灌,又从眼窝滴出来,落在铺着虎皮的地毯上。
“李将军,这可是用唐家翰林的骨头酿的好酒,埋在地下三年才开封,您尝尝?”
瘦高个把骷髅头往络腮胡面前递,“那老东西死前还骂咱们是乱臣贼子,如今还不是成了将军的酒器?”
沈青芜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酸水首往喉咙涌。
她刚要别过脸,却被络腮胡伸手按住肩膀。
那手掌像铁钳似的,指腹的老茧刮得她锁骨生疼,仿佛要嵌进骨头里。
“这小娘子看着面生。”
络腮胡的目光在她脸上逡巡,最后落在她怀里的琵琶上,“怀里揣着这物件,是教坊司的?”
沈青芜咬紧牙关没应声。
长安教坊司的嬷嬷说过,艺人的琴音里藏着骨头,该为知音弹,为山河弹,绝不能为豺狼弹。
当年杨贵妃的琵琶只弹给唐明皇听,如今就算长安破了,这规矩也不能破。
“嘿,还挺倔!”
瘦高个突然拔出腰间弯刀,寒光一闪,猛地劈向旁边的木案。
“咔嚓” 一声,半块没吃完的烤肉连带着木屑飞溅起来,其中一片带着油星擦过沈青芜的脸颊,在颧骨上留下道血痕。
“李将军问你话呢!
聋了不成?
信不信老子把你这破琴劈了当柴烧,再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刀锋离她的眼睛只有寸许,寒气逼得她睫毛发颤。
沈青芜死死盯着那把刀,刀柄上还缠着块褪色的红绸,像是哪家姑娘的嫁妆。
她突然想起教坊司的素云姐姐,嫁了个羽林卫,新婚那天就披红绸挂了彩,如今不知是死是活。
“住手。”
络腮胡挥了挥手,瘦高个的刀堪堪停在沈青芜眼前。
他接过沈青芜怀里的琵琶,翻来覆去地看,粗糙的手指抚过琴身的雕花,最后停在 “永保太平” 那西个字上。
“永保太平?”
他突然冷笑一声,笑声像破锣似的,“如今这世道,还保什么太平?”
话音未落,他竟抽出腰间匕首,寒光一闪,在那西个字上狠狠划了道十字。
木屑纷飞中,沈青芜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琴身的震颤顺着手臂传到心口,像是母亲在哭。
当匕首再次扬起,眼看就要刺穿琴箱时,她突然按住琴弦,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弹。”
指尖落在琴弦上的瞬间,她本想弹《广陵散》。
那曲子里有金戈铁马的烈气,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决绝,配得上这帐内的刀光剑影。
可琴弦震颤的刹那,黄河滩的浮尸、老者怀里的《论语》、教坊司染血的曲谱、母亲临终前望着长安方向的眼神,突然全涌进脑海。
琴音不受控制地软下来,竟成了《霓裳羽衣曲》的残调,断断续续的,像被风吹散的叹息。
帐内的喧哗突然静了。
络腮胡将军放下酒杯,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案几,节奏竟和琴音莫名合拍。
沈青芜低着头,看见他靴底沾着的泥块里,混着几缕暗红的丝线 —— 那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用的章服料子,和白马驿浮尸身上的紫袍一模一样。
“不对。”
络腮胡突然拍案而起,黄铜炭炉被震得一晃,火星溅出来落在沈青芜的脚踝上,烫得她猛地缩脚,却没敢发出声。
“这曲子太软,像没断奶的娃娃,配不上咱们朱王的功业!”
他一把揪住沈青芜的头发,将她的脸狠狠按向案上的盘子,“给我弹个快活的!
没听见弟兄们正吃着人肉脯吗?
得配着血光弹才够味!”
盘子里的肉片切得极薄,泛着诡异的粉红色,油光下隐约能看见指甲盖大小的月牙形白痕 —— 那是指甲的痕迹。
沈青芜胃里一阵痉挛,喉头涌上腥甜的血气。
她猛地抬头,发髻散开,青丝披在脸上,正好挡住络腮胡狰狞的眼神。
怀里的琵琶被她带得倾斜,琴弦骤然绷紧,“嘣” 的一声脆响,最粗的那根弦断了,锋利的断口在她指尖划开道血口子。
断弦像道银色的闪电,悬在半空,划破帐内凝滞的空气。
沈青芜看着指尖渗出的血珠滴在琴身,晕开一朵朵细小的红梅,沿着木纹往 “永保太平” 那西个字的刻痕里钻。
这场景竟和长安破城那日如此相似 —— 那天她也是这样抱着琵琶,琴弦断在朱漆廊柱上,血珠滴在母亲留下的《教坊记》上。
只是这次,再没人会温柔地用香膏给她包扎伤口,再没人会把她护在身后说 “青芜不怕”。
络腮胡将军盯着断弦看了半晌,突然爆发出粗野的大笑,震得帐顶的灰尘簌簌往下掉。
“好!
断得好!”
他抓起案上的酒壶,把剩下的酒全泼在琴身上,酒液混着血珠渗进木纹,在 “永保太平” 的刻痕里积成小小的水洼。
“就该用断弦弹这乱世!
从今天起,你就跟着老子,把咱们灭唐兴梁的功业,把这黄河滩的血色,全弹出来!”
沈青芜被两个士兵拖出帐篷时,正看见一轮残月从云缝里钻出来,惨白的光洒在营寨上,把连绵的帐篷照得像片坟茔。
远处传来女人压抑的哭嚎和男人的狞笑,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琵琶声 —— 不知是哪个教坊司的姐妹,正在为这些豺狼弹奏助兴。
那琴音慌乱得像惊弓之鸟,连最基础的指法都错了。
她摸了摸怀里的《教坊记》,手稿被汗水浸得发潮,母亲的字迹在黑暗中仿佛活了过来。
沈青芜把断弦捡起来,塞进琴箱夹层,那点尖锐的疼痛顺着指尖传遍全身,让她在麻木中清醒了几分。
活下去。
母亲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哪怕要用断弦弹尽这人间炼狱,哪怕要看着 “永保太平” 西个字被血浸透,也要活下去。
因为只有活着,才能记得住长安的月光,记得住《霓裳羽衣曲》本该有的模样,记得住白马驿的水里,那些沉下去的墨迹和骨头。
《五代离歌:琵琶血笺》精彩片段
咸通十西年的秋阳毒得像淬了火的烙铁,把黄河滩的芦苇烤得卷了边,空气里飘着股说不清的怪味 —— 有芦苇的焦糊气,有河水的腥臊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像陈年血痂被泡开的甜腥。沈青芜的布鞋在逃亡路上磨穿了底,露出的脚趾被河滩碎石划得血肉模糊,每走一步都像踩着碎玻璃,血珠混着泥水在沙地上拖出蜿蜒的红痕,没等干透就被后面的人踩成更深的污渍。
她怀里的琵琶被搂得死紧,桐木琴身被体温焐得发烫,琴箱里衬的软绸磨着锁骨,倒像是母亲临终前最后一次抚摸她的手。
那把琵琶是母亲的陪嫁,琴颈背面刻着极小的 “永保太平” 西个字,还是开元年间的老物件。
沈青芜总觉得那西个字里藏着母亲的魂,只要攥着琴,就不算彻底被抛在这乱世里。
“快走!
瞎磨蹭什么!”
粗粝的马鞭带着风声擦过耳畔,抽在旁边的芦苇丛里,惊起一群白鹭扑棱棱飞起。
沈青芜踉跄着往前扑,额头撞在前面妇人的背上,那妇人回过头,脸上满是煤灰般的污渍,唯有一双眼睛亮得吓人,像两簇濒死的炭火。
“小娘子,惜命就别停步。”
妇人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前儿个有个姑娘掉了队,被兵爷们拖进芦苇荡,出来时…… 只剩半截身子了。”
沈青芜猛地攥紧琵琶,指节泛白。
脖颈上还留着教坊司那串铜铃的勒痕,三天前朱温的士兵撞开宫门时,她就是被那串铃链拴在廊柱上。
铜铃在她挣扎时叮当作响,和姐妹们的哭嚎、士兵的狞笑混在一起,成了她对长安最后的记忆。
她眼睁睁看着教坊司的嬷嬷被一刀割破喉咙,鲜血溅在《霓裳羽衣曲》的曲谱上,把 “云想衣裳花想容” 染成了黑红色。
一阵更浓重的腥甜被风卷过来,带着河泥的腐臭。
沈青芜突然顿住脚步,像被看不见的线钉在了原地。
离岸半丈的浅水里,漂着个裹着紫袍的身影。
花白的胡须散开在浑浊的水面,像一蓬沉溺的水藻,而本该束着玉带的脖颈处,只剩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暗红的血在水里氤氲开来,像幅被揉皱的劣质水墨画。
沈青芜死死捂住嘴才没让尖叫冲破喉咙 —— 那身紫袍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章服,她在长安教坊司见过御史大夫穿同款,去年上元节,那位大人还捻着胡须听她弹《梅花三弄》,夸她 “指尖有风骨”。
“看什么看!
找死啊!”
押送的士兵踹在她后腰上,力道大得让她往前扑进水里。
冰凉的河水瞬间浸透粗布衣衫,冻得她牙关打颤,怀里的琵琶却被她高高举着,生怕沾了水。
挣扎着抬头时,视野里突然挤满了浮尸,像被秋风打落的残叶。
有的被箭钉在芦苇根上,箭杆上还挂着破烂的官袍;有的被拦腰斩断,肠肚在水里缓缓散开,引来成群的小鱼啄食;最让她脊背发寒的是个穿绯色官服的老者,怀里紧紧抱着一卷书,书页被水泡得发胀,露出 “论语” 两个洇湿的墨字,墨迹在水里晕开,像两行无声的泪。
“这是白马驿那帮老东西的下场!”
旁边的士兵啐了口唾沫,靴底碾过滩涂上的碎骨,“朱王说了,这些读死书的,总想着恢复大唐那套规矩,留着就是祸害!”
他突然扯住沈青芜的头发,把她的脸往水面按,“看清楚了!
以后见了咱们梁军的爷们,就该把头埋进裤裆里!
别学这些酸儒,死到临头还端着架子!”
河水呛进鼻腔,又辣又腥。
沈青芜在挣扎中看见那老者怀里的《论语》,突然想起母亲藏在《教坊记》夹层里的那句话:“乱世最狠的,从不是刀兵,是把人命当草芥的心思,是把诗书当粪土的狂妄。”
她猛地挣脱士兵的手,咳出满口河水,喉咙里火烧火燎地疼。
傍晚时分,她们被赶进一处临时搭建的营寨。
木栅栏歪歪扭扭,到处是没清理干净的血渍和粪便,几头瘦骨嶙峋的战马拴在桩上,啃着带泥的芦苇根。
沈青芜被两个士兵架着胳膊拖进最大的那顶帐篷,掀开帐帘的瞬间,浓重的酒气和血腥味扑面而来,熏得她几乎晕厥。
帐中央燃着个黄铜炭炉,火苗舔着炉壁,映得围坐的几个将领脸色忽明忽暗。
为首的络腮胡将军正举着个白玉酒杯,里面盛着暗红色的液体,在火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他对面的瘦高个将领谄媚地笑着,手里把玩着颗骷髅头,天灵盖上钻了个孔,用银链穿着,杯里的酒正顺着孔往骷髅头里灌,又从眼窝滴出来,落在铺着虎皮的地毯上。
“李将军,这可是用唐家翰林的骨头酿的好酒,埋在地下三年才开封,您尝尝?”
瘦高个把骷髅头往络腮胡面前递,“那老东西死前还骂咱们是乱臣贼子,如今还不是成了将军的酒器?”
沈青芜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酸水首往喉咙涌。
她刚要别过脸,却被络腮胡伸手按住肩膀。
那手掌像铁钳似的,指腹的老茧刮得她锁骨生疼,仿佛要嵌进骨头里。
“这小娘子看着面生。”
络腮胡的目光在她脸上逡巡,最后落在她怀里的琵琶上,“怀里揣着这物件,是教坊司的?”
沈青芜咬紧牙关没应声。
长安教坊司的嬷嬷说过,艺人的琴音里藏着骨头,该为知音弹,为山河弹,绝不能为豺狼弹。
当年杨贵妃的琵琶只弹给唐明皇听,如今就算长安破了,这规矩也不能破。
“嘿,还挺倔!”
瘦高个突然拔出腰间弯刀,寒光一闪,猛地劈向旁边的木案。
“咔嚓” 一声,半块没吃完的烤肉连带着木屑飞溅起来,其中一片带着油星擦过沈青芜的脸颊,在颧骨上留下道血痕。
“李将军问你话呢!
聋了不成?
信不信老子把你这破琴劈了当柴烧,再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刀锋离她的眼睛只有寸许,寒气逼得她睫毛发颤。
沈青芜死死盯着那把刀,刀柄上还缠着块褪色的红绸,像是哪家姑娘的嫁妆。
她突然想起教坊司的素云姐姐,嫁了个羽林卫,新婚那天就披红绸挂了彩,如今不知是死是活。
“住手。”
络腮胡挥了挥手,瘦高个的刀堪堪停在沈青芜眼前。
他接过沈青芜怀里的琵琶,翻来覆去地看,粗糙的手指抚过琴身的雕花,最后停在 “永保太平” 那西个字上。
“永保太平?”
他突然冷笑一声,笑声像破锣似的,“如今这世道,还保什么太平?”
话音未落,他竟抽出腰间匕首,寒光一闪,在那西个字上狠狠划了道十字。
木屑纷飞中,沈青芜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琴身的震颤顺着手臂传到心口,像是母亲在哭。
当匕首再次扬起,眼看就要刺穿琴箱时,她突然按住琴弦,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弹。”
指尖落在琴弦上的瞬间,她本想弹《广陵散》。
那曲子里有金戈铁马的烈气,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决绝,配得上这帐内的刀光剑影。
可琴弦震颤的刹那,黄河滩的浮尸、老者怀里的《论语》、教坊司染血的曲谱、母亲临终前望着长安方向的眼神,突然全涌进脑海。
琴音不受控制地软下来,竟成了《霓裳羽衣曲》的残调,断断续续的,像被风吹散的叹息。
帐内的喧哗突然静了。
络腮胡将军放下酒杯,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案几,节奏竟和琴音莫名合拍。
沈青芜低着头,看见他靴底沾着的泥块里,混着几缕暗红的丝线 —— 那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用的章服料子,和白马驿浮尸身上的紫袍一模一样。
“不对。”
络腮胡突然拍案而起,黄铜炭炉被震得一晃,火星溅出来落在沈青芜的脚踝上,烫得她猛地缩脚,却没敢发出声。
“这曲子太软,像没断奶的娃娃,配不上咱们朱王的功业!”
他一把揪住沈青芜的头发,将她的脸狠狠按向案上的盘子,“给我弹个快活的!
没听见弟兄们正吃着人肉脯吗?
得配着血光弹才够味!”
盘子里的肉片切得极薄,泛着诡异的粉红色,油光下隐约能看见指甲盖大小的月牙形白痕 —— 那是指甲的痕迹。
沈青芜胃里一阵痉挛,喉头涌上腥甜的血气。
她猛地抬头,发髻散开,青丝披在脸上,正好挡住络腮胡狰狞的眼神。
怀里的琵琶被她带得倾斜,琴弦骤然绷紧,“嘣” 的一声脆响,最粗的那根弦断了,锋利的断口在她指尖划开道血口子。
断弦像道银色的闪电,悬在半空,划破帐内凝滞的空气。
沈青芜看着指尖渗出的血珠滴在琴身,晕开一朵朵细小的红梅,沿着木纹往 “永保太平” 那西个字的刻痕里钻。
这场景竟和长安破城那日如此相似 —— 那天她也是这样抱着琵琶,琴弦断在朱漆廊柱上,血珠滴在母亲留下的《教坊记》上。
只是这次,再没人会温柔地用香膏给她包扎伤口,再没人会把她护在身后说 “青芜不怕”。
络腮胡将军盯着断弦看了半晌,突然爆发出粗野的大笑,震得帐顶的灰尘簌簌往下掉。
“好!
断得好!”
他抓起案上的酒壶,把剩下的酒全泼在琴身上,酒液混着血珠渗进木纹,在 “永保太平” 的刻痕里积成小小的水洼。
“就该用断弦弹这乱世!
从今天起,你就跟着老子,把咱们灭唐兴梁的功业,把这黄河滩的血色,全弹出来!”
沈青芜被两个士兵拖出帐篷时,正看见一轮残月从云缝里钻出来,惨白的光洒在营寨上,把连绵的帐篷照得像片坟茔。
远处传来女人压抑的哭嚎和男人的狞笑,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琵琶声 —— 不知是哪个教坊司的姐妹,正在为这些豺狼弹奏助兴。
那琴音慌乱得像惊弓之鸟,连最基础的指法都错了。
她摸了摸怀里的《教坊记》,手稿被汗水浸得发潮,母亲的字迹在黑暗中仿佛活了过来。
沈青芜把断弦捡起来,塞进琴箱夹层,那点尖锐的疼痛顺着指尖传遍全身,让她在麻木中清醒了几分。
活下去。
母亲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哪怕要用断弦弹尽这人间炼狱,哪怕要看着 “永保太平” 西个字被血浸透,也要活下去。
因为只有活着,才能记得住长安的月光,记得住《霓裳羽衣曲》本该有的模样,记得住白马驿的水里,那些沉下去的墨迹和骨头。
最新章节
同类推荐
猜你喜欢
 女王的「垂帘听政」(刘爱华汤普森)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女王的「垂帘听政」刘爱华汤普森
女王的「垂帘听政」(刘爱华汤普森)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女王的「垂帘听政」刘爱华汤普森
佚名
 雅典娜计划与「犯禁」的快感(高建国王奋斗)火爆小说_《雅典娜计划与「犯禁」的快感》高建国王奋斗小说免费在线阅读
雅典娜计划与「犯禁」的快感(高建国王奋斗)火爆小说_《雅典娜计划与「犯禁」的快感》高建国王奋斗小说免费在线阅读
佚名
 钟离低语声规则慕容思陆奕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钟离低语声规则全集免费阅读
钟离低语声规则慕容思陆奕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钟离低语声规则全集免费阅读
佚名
 富察复出(安凌安陵容)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富察复出(安凌安陵容)
富察复出(安凌安陵容)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富察复出(安凌安陵容)
佚名
 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
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
十三颗星星
 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
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
十三颗星星
 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完结版免费小说_完本小说大全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
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完结版免费小说_完本小说大全沼泽地的向日葵孟淮之淮之
十三颗星星
 热门小说《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小说免费阅读
热门小说《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小说免费阅读
梦几何
 热门小说《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小说免费阅读
热门小说《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小说免费阅读
梦几何
 热门小说《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小说免费阅读
热门小说《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换脸成敌国公主后,太子悔疯了!樊破月萧景逸小说免费阅读
梦几何
 私藏读物《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顾淮安苏念念全章节在线阅读_(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全集阅读
私藏读物《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顾淮安苏念念全章节在线阅读_(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全集阅读
苏茉茉莉
 私藏读物《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顾淮安苏念念全章节在线阅读_(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全集阅读
私藏读物《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顾淮安苏念念全章节在线阅读_(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全集阅读
苏茉茉莉
 私藏读物《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顾淮安苏念念全章节在线阅读_(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全集阅读
私藏读物《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顾淮安苏念念全章节在线阅读_(入殓师老婆在停尸间过夜,我果断离婚)全集阅读
苏茉茉莉
 热门小说(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安然宋时宴)全文免费阅读_《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完结版免费阅读
热门小说(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安然宋时宴)全文免费阅读_《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完结版免费阅读
白葵
 热门小说(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安然宋时宴)全文免费阅读_《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完结版免费阅读
热门小说(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安然宋时宴)全文免费阅读_《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完结版免费阅读
白葵
 热门小说(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安然宋时宴)全文免费阅读_《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完结版免费阅读
热门小说(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安然宋时宴)全文免费阅读_《外卖把我未婚先孕的孩子送到校门口后》完结版免费阅读
白葵
 《经年孤影难成双》谢临舟苏念月全文阅读_经年孤影难成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经年孤影难成双》谢临舟苏念月全文阅读_经年孤影难成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简图
 《经年孤影难成双》谢临舟苏念月全文阅读_经年孤影难成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经年孤影难成双》谢临舟苏念月全文阅读_经年孤影难成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简图
 《经年孤影难成双》谢临舟苏念月全文阅读_经年孤影难成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经年孤影难成双》谢临舟苏念月全文阅读_经年孤影难成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简图
 《轻烟白雾掩真心》薛照梨沈聿之全本在线阅读_(轻烟白雾掩真心)完整版在线阅读
《轻烟白雾掩真心》薛照梨沈聿之全本在线阅读_(轻烟白雾掩真心)完整版在线阅读
澄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