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条不归路(旷野荆岩)小说完整版_完结好看小说一条不归路旷野荆岩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藕霸哥哥
- 更新:2025-08-08 04:32:25
《一条不归路(旷野荆岩)小说完整版_完结好看小说一条不归路旷野荆岩》精彩片段
初秋的凉意渗入晨光,宽阔的国道旁喧嚣如沸。引擎轰鸣,车轮滚动,
离别的絮语与父母的叮咛交织成一片。轿车、火车、崭新的自行车,
载着一个个被期许包裹的年轻身影,这里像一个巨大的驿站,挤满了奔赴不同方向的人生。
引擎轰鸣,车轮滚动,混杂着父母殷切的叮咛与离别的叹息。轿车窗内,
母亲紧握着孩子的手,絮叨着远方的叮嘱;火车站的月台上,父亲拍着儿子的肩膀,
目光深沉;骑着崭新自行车的少年,意气风发,引来邻家羡慕的眼光。每一个孩子,
都乘着属于他们的“方舟”,汇入那条被千万人踏平、车辙深深的大路洪流。“孩子!回来!
” 母亲的声音穿透嘈杂,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哭腔,她焦急地指向那条车水马龙的国道,
“你看清楚!那儿,那儿哪有什么像样的路啊?全是野草、石头、没人去的荒地!
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安安稳稳地走这条大路?
” 她的眼神里盛满了忧虑和不舍,仿佛我即将踏入的不是一片土地,
而是一片吞噬希望的深渊。我下意识地紧了紧肩上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小包,
粗糙的木质拐棍在掌心传递着一种奇异的支撑感。那触感冰凉而坚实,
像是我此刻唯一能抓住的锚点。“妈,” 我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仿佛用尽了胸腔里积攒的所有勇气,“人生…不是只有规划好的道路。
它更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 说完,我用力地、几乎是决绝地挥了挥手,
不敢再看母亲眼中可能瞬间涌出的泪水,毅然转身,将身后那片喧嚣与担忧抛下,
踏上了那条与国道垂直分岔、深深没入荒草深处的小径。世界的喧嚣骤然被抽离,
只剩下风在草尖刮过的、单调而凄厉的呜咽,以及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真正的“旷野”在眼前铺展——连绵起伏、如同凝固的墨绿色巨兽般的山峦,
莽莽苍苍、望不到边际的原始森林,在稀薄的晨雾中透出亘古未开、寂寥又深不可测的寒意。
脚下?根本无路可言!只有零星被踩倒又顽强挺起的枯草,
在嶙峋怪石和带刺的灌木丛中艰难地指示着方向。我拄着拐棍,
每一步都深陷在松软的腐殖土或硌脚的碎石中,翻越陡峭得令人窒息的山脊,
趟过冰冷刺骨、几乎冻僵脚踝的溪流。汗水很快浸透单衣,又在山风里迅速变得冰冷黏腻。
孤独,如同冰冷的毒蛇,随着每一次疲惫到极致的喘息,缠绕上四肢百骸,勒紧心脏。
初时那点“旷野”的豪情,在这无边的死寂和步步维艰中,被反复捶打、消磨殆尽。
暮色四合的速度比预想中快得多。铅灰色的云层沉沉压下,光线迅速被密林吞噬。
一种原始的不安攫住了我。就在我试图加快脚步,寻找一处相对安全的露宿点时,
一阵异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嗥声,毫无征兆地从侧后方的灌木丛中传来!那声音,
低沉、沙哑,充满了饥饿与残忍的意味。我猛地顿住脚步,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僵硬地转过头——昏暗中,几双闪烁着幽绿荧光的眼睛,如同鬼火般,
在茂密的荆棘丛后死死锁定了我!是豺!而且不止一只!它们无声无息地潜行着,
瘦骨嶙峋的身躯在枯草间若隐若现,腥膻的气味随着山风飘来,令人作呕。
恐惧像冰冷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所有理智。我几乎是本能地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
转身拔腿就跑!什么疲惫,什么孤独,统统被求生的本能碾碎!身后,
豺狼兴奋而瘆人的嗥叫声陡然拔高,利爪扒地的“沙沙”声如同催命的鼓点,急速迫近!
我拼命狂奔,肺部火烧火燎,心脏几乎要炸开胸膛!荆棘撕扯着裤腿,
尖锐的岩石硌得脚底生疼。慌乱中,我被一块突起的树根狠狠绊倒,整个人重重地扑倒在地,
手中的拐棍脱手飞出老远!膝盖和手肘传来钻心的剧痛,更致命的是,这一摔,
彻底断绝了逃生的希望!腥风扑面!我绝望地蜷缩身体,
余光瞥见一道黄褐色的影子带着恶臭的腥风,凌空向我扑来!那闪着寒光的獠牙,
直逼我的咽喉!时间仿佛凝固,死亡的阴影冰冷地笼罩下来。“孽畜!滚开!!!
”千钧一发之际,一声炸雷般的怒吼,裹挟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猛地撕裂了死亡的寂静!
紧接着,一团炽热的、跳跃着橘红色光芒的火球,带着灼热的气息和噼啪作响的爆裂声,
如同陨星般,狠狠砸向我扑来的豺狼!“嗷呜——!”一声凄厉的惨嚎响起。
那扑到半空的豺狼被燃烧的火把砸中侧脸,皮毛瞬间焦糊,剧痛让它狼狈地翻滚开去。
另外几只逼近的豺狼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光和怒吼震慑,惊疑不定地停下脚步,
发出威胁的低吼,幽绿的眼睛在火光映照下闪烁着惊惧。我惊魂未定,
心脏狂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浑身抑制不住地剧烈颤抖。只见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如同天神降临般,挡在了我和豺狼之间!他一手紧握着一根粗壮坚韧、顶端削尖的木杖,
另一只手高高举起一根熊熊燃烧的火把!跳跃的火光勾勒出他棱角分明的侧脸,
汗水混合着尘土,眼神却如同燃烧的炭火,锐利、坚定,充满了无畏的怒火。“起来!
快到我身后!”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目光死死锁住那几只逡巡不前的豺狼,火把在他手中划出威慑性的弧线,火星四溅。
求生的本能让我爆发出最后的力量,连滚带爬地抓起掉落的拐棍,
手脚并用地挪到他高大身影投下的安全阴影里。他像一座沉默的山岳,将我完全护住。
豺狼显然被这勇猛的人类和持续燃烧的火焰震慑住了。它们不甘地低吼着,
在原地焦躁地踱步,幽绿的眼睛死死盯着跳跃的火光,
最终在头狼那只被烧伤的一声短促的呜咽后,夹着尾巴,
飞快地窜入更深的黑暗密林之中,消失不见。
只留下空气中淡淡的焦糊味和令人心悸的腥膻气。直到最后一点绿光也消失在黑暗中,
那个高大的身影才缓缓转过身,放下火把,警惕地环视了四周一圈,确认安全无虞后,
才将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神依旧锐利,但已褪去了方才的杀伐之气,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和审视。“没事了。”他的声音缓和下来,
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你受伤了?” 他蹲下身,目光扫过我擦破的手肘和膝盖。
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透了里衣,
劫后余生的巨大虚脱感让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力地摇头,指了指喉咙,
又指了指那些豺狼消失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感激和后怕。他点点头,
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荒野里,豺狼成群,尤其傍晚,最是凶险。一个人走,太冒险。
”他站起身,将火把插在旁边的泥土里,温暖的光圈驱散了浓重的暮色和寒意。“我叫荆岩。
”他简洁地自我介绍,向我伸出一只布满厚茧却沉稳有力的大手。“谢…谢谢你!荆岩大哥!
”我借着拐棍的力量,挣扎着站起,紧紧握住他的手,
那粗糙的触感传递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可靠,“我叫林野。
刚才…刚才要不是你…” 回想起那獠牙逼近的瞬间,我仍心有余悸,声音带着哽咽。
“举手之劳。”荆岩摆摆手,脸上露出一抹朴实却真诚的笑容,“在这片旷野里,
能相遇就是缘分。总不能见死不救。”他弯腰捡起自己的木杖,
又帮我将脱手的拐棍拾回递给我,“天快黑了,这里血腥气重,不安全。
前面不远有个避风的小岩凹,我在那里生了火堆。跟我来?”我忙不迭地点头,
此刻他就像黑暗中唯一的光源,是我全部的安全感来源。我们借着火把的光芒,
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去。很快,
一个小小的、被岩石半包围的浅凹出现在眼前,里面果然跳跃着一堆温暖的篝火,
旁边散落着简单的行囊和一个取水的皮囊。围着篝火坐下,
温暖驱散了身体的寒冷和心头的恐惧。荆岩从行囊里翻出一个小陶罐,
倒出些清水浸湿一块干净的粗布,递给我:“擦擦伤口。”我感激地接过,
一边处理着皮外伤,一边忍不住再次道谢:“荆岩大哥,真的…太感谢了!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恐怕…”荆岩往火堆里添了根柴,火苗噼啪作响,
映照着他坚毅的侧脸。“我也曾差点死在狼吻之下,是路过的一位采药老人救了我。
在这旷野里行走,危险是常态,但守望相助,也是这里的法则。”他看向我,眼神深邃,
“看你这样子,不像猎户采药人,也不是商旅。为什么一个人走这‘野径’?”他这一问,
瞬间点燃了我心中积压已久的倾诉欲。我放下布巾,深吸一口气,将母亲在国道旁的阻拦,
自己“人生是旷野”的信念,以及踏上这条路的孤寂、艰辛,还有刚才那濒死的恐惧和绝望,
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说到母亲质疑“那儿有什么路”时,
声音里充满了迷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荆岩静静地听着,篝火在他眼中跳跃。待我说完,
他沉默了片刻,忽然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笑声中带着理解与共鸣。
“好一个‘人生是旷野’!”他赞赏地看着我,“你母亲眼中的‘死路’,
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才是通往‘大道’的活路。”他拿起一根树枝,
在篝火旁松软的泥土上画了一条蜿蜒的线,“你看这路,它不在现成的地图上,
它在我们脚下,在我们心里。那些走国道的人,他们到达的,是别人设定的终点。
而我们走这‘野径’,寻找的,是属于自己的‘道’。”“道?”我咀嚼着这个字眼。“对,
‘大道’。”荆岩的眼神变得无比明亮,仿佛有星辰在其中燃烧,“它不是功名利禄,
而是生命的本真,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是超越俗世束缚的精神追求。就像这山中的风,
林间的泉,看似无形无迹,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他顿了顿,看着我,
“你选择踏入这旷野,忍受孤独,直面生死,不正是为了追寻心中那个模糊却执着的念头吗?
那,就是你的‘道’的萌芽。”他的话,如同醍醐灌顶!
瞬间驱散了我心中因遇险和母亲质疑而笼罩的所有阴霾!
那种找到知音、灵魂被理解的巨大震撼和狂喜,几乎让我热泪盈眶!
我激动地追问:“荆岩大哥,你…你也是追寻这‘大道’的人?”荆岩点点头,
笑容温暖而坚定:“是。我曾在繁华的城镇中迷失,被俗世的枷锁束缚得喘不过气。
直到有一天,我翻开一本残破的《庄子》,读到‘逍遥游’,读到‘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灵魂属于这片旷野,
属于对‘大道’的追寻。于是我抛弃了所有,就像你一样,只带着一根木杖和一点干粮,
走了进来。”他拍了拍身边的木杖,顶端似乎刻着一些古老的纹路。篝火噼啪作响,
我们的话题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从老庄的玄思到孔孟的入世精神,
从山间草木蕴含的哲理到星辰流转昭示的宇宙规律,
才对抗豺狼时体验到的生死一线的感悟到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荆岩的见解深刻而独到,
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却又带着荒野赋予的质朴与豁达。
他讲述他在峭壁上观察鹰隼翱翔领悟的自由,在暴风雨中感受自然的伟力与自身的渺小。
我则分享我一路跋涉的见闻,那些触动心灵的微小事物,以及心中种种尚未成型的困惑。
我们并肩坐在一块巨大的、被阳光晒得微暖的青石上。交谈像山涧清泉般自然流淌。
从为何选择这条看似无路的“野径”,到各自追寻的目标——那并非世俗的名利,
而是某种难以言喻的、关乎生命本源与真理的“大道”。他的话语精辟而深邃,
对古老经典的见解让我茅塞顿开;我分享的旅途见闻和思考,也让他眼中闪烁着共鸣的光芒。
我们谈论星辰的轨迹,谈论草木的枯荣,谈论内心的困惑与坚持。
告别了那处曾弥漫着血腥与温暖篝火的岩凹,我和荆岩踏着晨露继续深入旷野。有了同伴,
跋涉的艰辛似乎也化作了砥砺意志的乐章。荆岩的荒野经验丰富,
辨识方向、寻找水源、规避险地都信手拈来,我则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我们时而沉默赶路,
感受天地间的肃穆;时而热烈讨论,思想的火花在崎岖山路上碰撞。
那场生死边缘的相遇与篝火旁的深谈,已将我们紧密联结。
翻越一道植被稀疏、怪石嶙峋的巨大山梁后,眼前豁然开朗。不再是压抑的密林,
而是一片相对平缓、布满巨大青石和低矮松柏的谷地。
一条清澈见底、水声淙淙的小溪蜿蜒穿过谷底。最令人惊异的是,在溪流对岸,
依着一块巨大的、如同屏风般的岩壁,竟搭着一间极其简陋却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的茅屋。
屋顶覆盖着厚厚的松针和苔藓,墙壁是就地取材的圆木和泥坯,
屋前用溪石垒砌出一个小小的平台,平台上放着几个手工粗糙的石墩。
袅袅炊烟正从茅屋后升起,融入清晨微凉的空气中。“有人!”荆岩低声道,
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在这人迹罕至的旷野深处,竟有隐居者?我们涉过清凉的溪水,
踏上那片石台。茅屋的木门虚掩着,门扉上挂着一串风干的松果和几片奇特的羽毛,
随风发出细微的碰撞声。正当我们犹豫着是否要出声询问时,门“吱呀”一声从内拉开。
一位老者出现在门口。他须发皆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用一根木簪束在脑后。面容清癯,
布满了岁月刻下的深深沟壑,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清澈,如同山巅未被尘埃沾染的湖泊,
沉淀着无垠的智慧和一种洞悉世事的平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着几处补丁的麻布长袍,
身形瘦削却挺拔如松,仿佛已与身后的山岩融为一体。他手中捧着一个陶土烧制的简陋茶壶,
热气氤氲。“远道而来的客人,山风清冽,且饮一杯粗茶暖暖身子。”老者的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温和而沉稳,仿佛山涧流淌的清泉,
瞬间抚平了我们跋涉的疲惫和初见的局促。我们连忙躬身行礼。
同类推荐
 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完整免费小说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
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完整免费小说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
恕盲
 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
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
恕盲
 脱掉渣男,我成了自己的光林小雨陈朗热门完本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脱掉渣男,我成了自己的光(林小雨陈朗)
脱掉渣男,我成了自己的光林小雨陈朗热门完本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脱掉渣男,我成了自己的光(林小雨陈朗)
展尘聆心
 《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家草哪有野草香》全集阅读
《家草哪有野草香》马锦姝赵卓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家草哪有野草香》全集阅读
恕盲
 林薇林远《第十一次婚宴请柬》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林薇林远)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林薇林远《第十一次婚宴请柬》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林薇林远)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Tim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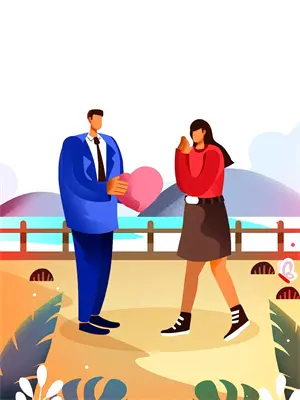 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凌清寒虞弦)全本免费小说阅读_全文免费阅读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凌清寒虞弦
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凌清寒虞弦)全本免费小说阅读_全文免费阅读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凌清寒虞弦
卿青穗祟
 凌清寒虞弦(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最新章节列表_(凌清寒虞弦)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最新小说
凌清寒虞弦(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最新章节列表_(凌清寒虞弦)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最新小说
卿青穗祟
 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凌清寒虞弦)完结版免费阅读_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全文免费阅读
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凌清寒虞弦)完结版免费阅读_修仙界团宠他靠海王人设躺赢全文免费阅读
卿青穗祟
 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山吹山吹)最新小说
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山吹山吹)最新小说
这术可真术啊
 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山吹山吹)最新热门小说_完结小说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山吹山吹)
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山吹山吹)最新热门小说_完结小说今天也喜欢狗卷同学(山吹山吹)
这术可真术啊







